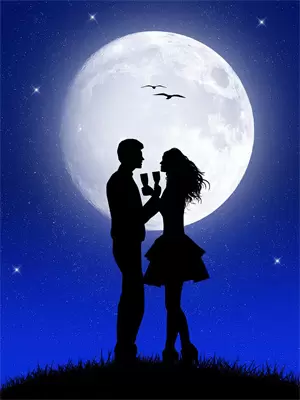1 序章 梦回宣和## 序章 梦回宣和宣和六年的汴京,繁华得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。
御街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,叫卖声、丝竹声、马蹄声混杂在一起,汇成一股喧闹的暖流,
涌动着这座百万人口都城的脉搏。
空气中弥漫着脂粉香、食物的香气与一丝若有若无的尘土气,这是独属于大宋盛世的味道,
浓烈而醉人。林羽蜷缩在州桥下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,
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衫早已被露水打湿,冰冷地贴在身上。
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支快要用秃的毛笔,面前摊着几张粗糙的草纸,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。
那字迹颇为古怪,既有楷书的工整,又夹杂着许多简化的笔画,在旁人看来,
简直就是不伦不类的“鬼画符”。可对林羽而言,这是他唯一的慰藉,
是他与那个遥远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。三个月前,他还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系研究生林薇,
在实验室里整理一份关于宋代漕运的文献时,一道诡异的电弧闪过,他便失去了意识。
再次醒来,就成了这个十七岁的破落书生林羽。原主因家道中落,又屡试不第,郁郁而终,
恰好给了他这个异世的灵魂一个栖身之所。起初的惊恐与茫然过后,
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宣和六年,靖康之耻前夜,一个行将就木的华丽王朝,
一个即将被铁蹄踏碎的文明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骨节分明却略显苍白的手,这双手,
既拿过现代的鼠标键盘,也握过宋代的毛笔。他摸了摸胸口,那里悬着一枚温润的玉佩,
是穿越时唯一带来的东西,也是他身份认同的最后凭证。
路过的行人偶尔投来好奇或鄙夷的目光,他早已习惯。在这个世界,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存在,
一个靠抄书勉强糊口的穷书生。“林夫子,又在这儿写你的‘天书’呢?
”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。林羽抬头,是隔壁卖炊饼的武大郎。他憨厚地笑着,
递过来一个热气腾腾的炊饼,“刚出炉的,垫垫肚子吧。”林羽接过炊饼,
暖意从手心传到心里,他点了点头,沙哑地道了声谢。他知道,在这冰冷的陌生世界里,
这点微不足道的善意,是他活下去的动力。他咬了一口炊饼,目光却越过熙攘的人群,
望向皇城的方向。那座金碧辉煌的宫城,此刻正被一个叫赵佶的艺术家皇帝和他的宠臣们,
一步步推向深渊。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抄书换不来温饱,更换不来一个国家的未来。
他必须做点什么,哪怕只是螳臂当车。
---2 第1章 奇策初显## 第1章 奇策初显天刚蒙蒙亮,
汴京的早市已经热闹起来。林羽没有再去州桥下抄书,
而是揣着那几张写满“鬼画符”的草纸,径直走向了城南的农具市场。他身上那件青衫依旧,
但眼神却不再是之前的迷茫,而是透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。他知道,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。
想要在这个世界立足,第一步,先生存下去。他在市场里转悠了大半天,
仔细观察着各式各样的农具。曲辕犁、耧车、水碓……这些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古物,
如今就活生生地摆在他面前。他发现,这些农具虽然设计巧妙,但效率普遍不高,
尤其是灌溉用的水车,耗费人力巨大,引水量却有限。一个念头在他脑中逐渐成形。
他在一家铁匠铺前停下了脚步,铺子的老师傅正叮叮当当地打着一把菜刀。林羽等他打完,
才上前拱了拱手:“老师傅,打扰了。学生有个想法,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老师傅抬起头,
打量了他一番,看他虽衣着寒酸,但眉清目秀,不像个市井无赖,便道:“但说无妨。
”林羽从怀里掏出草纸,铺在满是铁屑的案台上,
指着上面一个简陋的图形说:“学生见这龙骨水车,虽好,却费力。
若将此处的踏板改为齿轮,再以牛力或水力驱动,岂不省时省力?”老师傅凑过去一看,
那图形歪歪扭扭,但结构却颇为新奇。他是个行家,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,
不由得瞪大了眼睛:“你这……这是啥玩意?齿轮?老汉我打了一辈子铁,没见过这种东西。
”“此乃‘齿轮传动’之理,”林羽耐心解释道,“大轮转一圈,小轮转数圈,
以小力博大用。若能造出此物,引水效率可增三倍不止。”老师傅将信将疑,
但林羽眼中那股笃定的光芒,让他有些心动。他沉吟片刻,道:“想法是好,
可这玩意儿造出来,谁用?又谁信?”林羽微微一笑,胸有成竹地说:“老师傅若愿一试,
学生愿立下字据,若此物无用,学生愿赔上所有工本钱。若是有用,这汴京周边的田地,
还愁没销路吗?”接下来的几天,林羽几乎就泡在了这家铁匠铺里。
他凭着大学时学过的机械原理知识,手把手地指导老师傅打造齿轮和轴承。没有现代的机床,
他们就靠最原始的锻打和锉磨,一点点地修正。林羽的手上很快磨出了血泡,但他毫不在意。
当第一台简陋的“齿轮水车”终于成型时,他累得几乎虚脱,
但看着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金属齿轮,心中却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他知道,
这是他改变历史的第一步,虽然微小,却无比坚实。
---3 第2章 聚贤初逢## 第2章 聚贤初逢齿轮水车造出来的消息,
像一阵风似的在城南传开了。起初是看热闹的,后来是半信半疑的农夫,
最后连一些乡绅也派了管家来打听。林羽和铁匠师傅在城外的护城河边做了一场演示。
当那头老牛慢悠悠地拉着大木轮,水车便发出一阵平稳的“咯吱”声,
清澈的河水被源源不断地提上岸,流入干涸的田垄时,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阵惊叹。
“神了!真是神了!”一个老农摸着那哗哗作响的水流,激动得老泪纵横,“有了这宝贝,
俺们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!”乡绅的管家们也纷纷上前,询问价格和订制事宜。
林羽并没有趁机抬高价钱,而是定了一个合理的价格,
并承诺可以教授使用和简单的维修方法。他深知,得民心者得天下,这不仅仅是一门生意,
更是他扎根于此的根基。齿轮水车的成功,让“林夫子”这个名号在汴京的市井间悄然传开。
人们不再只把他当成一个穷酸书生,而是看作一个有奇思妙想的“怪才”。有了些名气,
林羽的生活也好了起来,至少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。
他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下一步的计划。这天,他正在一家名为“聚贤楼”的茶馆里,
一边喝茶,一边听着说书先生讲《三国》。茶馆里人声鼎沸,三教九流汇聚于此,
是收集消息的绝佳场所。他正听得入神,邻桌的一番对话却吸引了他的注意。“……依我看,
那燕云十六州之事,朝廷当断不断,必受其乱!”一个清朗而有力的声音说道,
带着少年人的锐气。“赵兄小声些!”另一个声音紧张地劝道,
“这话要是被李相公的人听了去,可有你好果子吃。如今朝堂之上,谁敢提‘战’字?
”林羽循声望去,只见邻桌坐着两个年轻人。说话的那个,锦衣玉带,面容英挺,
眉宇间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英气,腰间还佩着一柄长剑。他虽在极力压低声音,
但那股愤懑之气却怎么也掩不住。林羽心中一动,这不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同道中人吗?
他端着茶杯,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,对着那锦衣少年拱了拱手:“在下林羽,
无意间听到兄台高论,深感钦佩。不知可否坐下,共饮一杯?”那锦衣少年抬起头,
警惕地打量着林羽。他的同伴则拉了拉他的衣袖。林羽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,
眼神清澈而真诚。少年犹豫了一下,还是点了点头:“在下赵轩。请坐。”林羽坐下,
也不绕弯子,直接说道:“赵兄方才所言,深得我心。然则,空谈误国。金人狼子野心,
辽国已是日薄西山,我大宋若不早做打算,唇亡齿寒之祸,不远矣。
”赵轩眼中闪过一丝惊讶,他没想到一个衣着普通的书生,竟有如此见识。
他追问道:“依林兄之见,又当如何?”林羽压低了声音,一字一句地说道:“联金灭辽,
乃是饮鸩止渴。当务之急,非是北伐,而是固本。整顿边防,练兵强军,同时安抚民心,
充实国库。待金辽两败俱伤,我大宋方可坐收渔翁之利。”这一番话,如同一道惊雷,
在赵轩耳边炸响。他看着眼前这个青衫书生,眼神从最初的警惕,变成了震惊,
再到深深的欣赏。他知道,自己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高人。
---4 第3章 花石之弊## 第3章 花石之弊与赵轩的相遇,
像是在林羽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,激起了层层涟漪。两人一见如故,
从天下大势谈到兵法谋略,常常在聚贤楼一坐就是一下午。赵轩出身将门,
父亲是兵部侍郎赵喆,自幼受忠君报国的思想熏陶,对朝政的腐败深恶痛绝。
林羽的许多“奇谈怪论”,比如“民生为本”、“历史周期律”,虽然他听得一知半解,
却总能切中要害,让他有种醍醐灌顶之感。林羽也通过赵轩,了解到了更多朝堂内部的秘闻。
他知道,宰相李邦彦靠着溜须拍马深得宋徽宗宠信,党羽遍布朝野,把持朝政。
而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,则备受打压。其中,最让百姓怨声载道的,莫过于“花石纲”。
为了满足宋徽宗对奇花异石的病态爱好,朝廷在江南设立了“苏杭应奉局”,
由朱勔父子主持,专门搜刮民间的奇石、古木、花竹。凡是百姓家中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,
便被贴上黄封,强行征用。运送这些“花石纲”的船队,首尾相连,绵延数里,
不仅耗费了巨额的钱财,更严重的是,为了给这些“贡品”开路,
沿途的桥梁、城墙、民宅被肆意拆毁,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“简直是祸国殃民!
”赵轩在聚贤楼里愤愤地捶着桌子,“我父亲曾数次上书弹劾朱勔,
却被李邦彦那厮以‘陛下雅好’为由驳回。如今,两浙路方腊之乱虽已平定,但民怨未消,
长此以往,国将不国!”林羽静静地看着他,心中却有了计较。他知道,
要撼动李邦彦的根基,从“花石纲”入手,是最好的突破口。这不仅能为百姓除害,
更能打击李邦彦的党羽,削弱他的势力。“赵兄,光生气是没用的。”林羽缓缓开口,
“要解决问题,得找到问题的根源。这花石纲,表面上是朱勔作恶,
根子却在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,但赵轩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根子,
在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身上。赵轩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,他虽然正直,
但“忠君”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,让他去非议皇帝,是他无法想象的。林羽看出了他的顾虑,
换了个方式说:“我们不必直接针对官家。我们可以让官家自己看到‘花石纲’的危害。
眼见为实,耳听为虚。”“如何让官家看到?”赵轩不解地问。林羽微微一笑,
眼中闪过一丝狡黠:“赵兄可听说过‘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’?既然官家喜欢奇石,
我们就给他一块‘奇石’。一块能说话的‘奇石’。”接下来的几天,
林羽把自己关在租来的小屋里,埋头写写画画。他利用自己现代的知识,
结合宋代的笔墨纸砚,绘制了一幅长卷。这幅长卷,一半是汴京的繁华景象,高楼林立,
歌舞升平;另一半,则是江南的凄惨景象,被拆毁的房屋,流离失所的百姓,
以及那些运送“花石纲”的官差如何横行霸道。他用最朴实的笔触,
将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并置在一起,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。画卷的末尾,
他题了一首小诗:“江南万民苦,只为君一石。若知民间事,应悔此生痴。
”他将这幅画卷取名为《汴京梦华图》,交给了赵轩。“赵兄,你父亲是兵部侍郎,
有向皇帝递折子的权利。这幅画,或许比千言万语更有用。”赵轩接过画卷,展开一看,
瞬间被震撼了。那画中百姓的苦难,仿佛要穿透纸背,扑面而来。他深吸一口气,
郑重地对林羽说:“林兄,此计若成,你便是我赵轩的再生父母!我这就回去,
想办法让我父亲见到这幅画。
---5 第4章 棋高一着## 第4章 棋高一着赵轩拿着那幅《汴京梦华图》回到家,
心中忐忑不安。他知道此举风险极大,一旦被李邦彦的人抓住把柄,说他“妖言惑众”,
不仅他自己,连他父亲赵喆都可能被牵连。但他一想到画中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,
想到林羽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,便下定了决心。他找到父亲赵喆,将画卷呈上,
并详细说明了林羽的计策。赵喆是个正直的老臣,看到画卷上的情景,气得浑身发抖。
他拍案而起,骂道:“朱勔误国!李邦彦谄媚!如此下去,我大宋危矣!”他当即决定,
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,也要将这幅画呈给宋徽宗。第二天早朝,赵喆在奏报完军务后,
出列奏道:“陛下,臣近日偶得一画,名曰《汴京梦华图》,请陛下御览。
”宋徽宗正有些昏昏欲睡,一听有新画,顿时来了兴趣。他酷爱书画,自诩“天下一人”,
对任何艺术品都有浓厚的兴趣。太监将画卷缓缓展开,宋徽宗起初还饶有兴致地看着,
但当他看到画卷后半部分那凄惨的景象时,脸色渐渐沉了下来。“这是何人所画?
简直是一派胡言!”站在一旁的李邦彦立刻跳了出来,
他一眼就看出这幅画是在影射“花石纲”,这无异于是在打他的脸。
赵喆不卑不亢地回道:“此画乃一民间画师所作,所绘皆是实情。陛下,
‘花石纲’劳民伤财,两浙路民怨沸腾,方腊之乱便是前车之鉴。若不加以制止,
恐再生大乱啊!”“放肆!”李邦厉声呵斥,“赵侍郎,你竟敢在朝堂之上危言耸听,
污蔑圣上雅好,是何居心?”宋徽宗的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。他是个艺术家,不是个政治家。
他喜欢美好的东西,厌恶一切丑陋和悲伤。这幅画让他感到很不舒服,
仿佛有人在指责他的过错。他沉声道:“够了!一幅画而已,怎能当真?花石纲乃朕之意,
为的不过是装点园林,与国何干?赵喆,你退下吧!”赵喆还想再劝,
却被宋徽宗一个眼神制止了。他只能无奈地退回班中,心中一片冰凉。
李邦彦则露出了得意的笑容,他知道,皇帝已经被他牢牢掌控。然而,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
宋徽宗虽然嘴上不说,但那幅画却像一根刺,扎在了他的心里。他回到后宫,越想越不对劲。
他是个自负的人,他不能容忍自己的“雅好”被说成是“祸国”。于是,
他私下里派了一个心腹太监,悄悄前往江南,去探查“花石纲”的实情。
这个心腹太监名叫童贯,是“六贼”之一,但与李邦彦面和心不和。他到了江南一看,
才发现情况比画中描绘的还要严重。当地的百姓对“花石纲”恨之入骨,
甚至有人编了歌谣来咒骂朱勔。童贯不敢隐瞒,将实情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宋徽宗。
宋徽宗看完童贯的密报,沉默了很久。他终于意识到,
自己的“雅好”确实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他虽然昏聩,但并非完全没有良知。几天后,
他下了一道圣旨,罢免了朱勔的官职,并下令缩减“花石纲”的规模。消息传来,
汴京的市井间一片欢腾。林羽听到这个消息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知道,
这是他们取得的第一次小小的胜利。虽然没能彻底根除“花石纲”,但至少,
让皇帝看到了真相,也让李邦彦的势力受到了一次打击。更重要的是,这次胜利,
让他和赵轩的信心都大增。他们相信,只要坚持下去,一定能给这个腐朽的王朝,
带来一丝改变的希望。
---6 第5章 太学风云## 第5章 太学风云“花石纲”事件的胜利,
让林羽在赵轩心中的地位愈发崇高。他不再将林羽仅仅看作一个有奇谋的朋友,
而是视作能指点迷津的良师。他意识到,林羽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在市井之间,
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施展抱负。而这个舞台,就是太学。“林兄,以你的才学,
终日埋首于市井,太过屈才了。”赵轩在聚贤楼里,郑重地对林羽说,“再过几月,
便是太学补试之日。你若能入太学,便有了入仕的资格,方能真正地为国效力。
”林羽心中何尝没有这个想法。他知道,在这个时代,要想改变什么,必须先进入体制内。
他点了点头:“赵兄所言极是。只是,我出身寒微,又无名师引荐,想要通过补试,
恐怕不易。”“这个你不用担心。”赵轩拍着胸脯说,“太学之中,
有不少与我志同道合的同学。我这就去为你奔走,让他们都认识一下你这位‘林夫子’。
你的那些‘奇思妙想’,定能让他们折服。”在赵轩的引荐下,
林羽开始出入太学附近的文人雅集。他凭借着对历史走向的精准预判和对时局的独到分析,
很快就吸引了一批思想开明、心怀报国之志的大学生。他们围在林羽身边,
听他讲“经世致用”之学,讲“富国强兵”之策。林羽那些超越时代的思想,如同一股清流,
让这些被困在故纸堆里的年轻人耳目一新。然而,
林羽的“异端邪说”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。其中,就包括太学博士李邦彦的侄子李孝严。
李孝严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,靠着叔叔的关系在太学里作威作福。他看不惯林羽一个穷书生,
竟然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拥戴,处处与他作对。“林羽,你一个靠抄书为生的贱民,
也敢妄议国事?你那些什么‘民生为本’,简直是离经叛道!”在一次雅集上,
李孝严当众发难。林羽淡淡地看了他一眼,说道:“《孟子》有云:‘民为贵,社稷次之,
君为轻。’李博士饱读诗书,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?”“你……你竟敢断章取义,
曲解圣人之言!”李孝严气得满脸通红。“我是否曲解,在座各位自有公论。
”林羽转向周围的太学生,“我大宋立国百年,为何积贫积弱?正是因为我等读书人,
只知空谈心性,不知体察民情。国家之根基在于民,民不聊生,国何以安?”林羽的一番话,
掷地有声,赢得了在场大多数大学生的赞同。李孝严见势不妙,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
但他对林羽的恨意,却更深了。太学补试那天,林羽沉着冷静地走进考场。
考题是“论边防之策”。这正是他最擅长的领域。他提笔挥洒,
将现代的军事思想与宋代的实际情况相结合,
提出了“精兵简政”、“屯田戍边”、“发展火器”等一系列主张。他的文章,逻辑严密,
论证充分,见解独到,让主考官们眼前一亮。放榜那天,林羽的名字赫然列在榜首。
他成功考入了太学,成为了一名上舍生。这意味着,他离自己的目标,又近了一大步。
他知道,从踏入太学的那一刻起,他就正式进入了这个时代的权力博弈场。前方的道路,
将更加凶险,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---7 第6章 御史之剑## 第6章 御史之剑进入太学,对林羽而言,
就像是鱼儿游入了大海。他有了更多接触高层信息的机会,
也有了更多结交志同道合之士的平台。他与赵轩以及一群思想进步的太学生,
形成了一个小团体,他们时常在一起探讨时弊,针砭时政,
被太学里的保守派私下称为“清流党”。林羽并没有因为考入太学而忘记自己的初心。
他利用太学丰富的藏书,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这个时代的知识,
同时也在暗中观察着朝堂上各方势力的消长。他知道,
李邦彦虽然因为“花石纲”事件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,但他的根基并未动摇,
依然牢牢地掌控着朝政。“林兄,如今我们身在太学,总不能一直纸上谈兵吧?
”赵轩有些焦急地说,“李邦彦那厮,最近又开始鼓动官家与金国结盟,想要联金灭辽。
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啊!”林羽点了点头,神情凝重:“我知道。联金灭辽,是下下之策。
辽国虽然腐朽,但毕竟是我大宋与金国之间的屏障。辽国一亡,金国铁骑便可长驱直入,
直抵黄河。我必须想办法阻止这件事。”“可是,我们人微言轻,
如何能阻止得了官家的决定?”赵轩有些泄气。林羽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:“人微言轻,
不代表无能为力。赵兄,你可知道御史台?”御史台,是宋代负责监察百官的机构,
权力极大。御史台的官员,被称为“言官”,可以“风闻言事”,即根据传闻弹劾官员,
而不需要拿出确凿的证据。这是林羽眼中,一把可以用来对抗李邦彦的利剑。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让我们去考御史?”赵轩有些不敢相信。“不,是我。”林羽平静地说,
“太学上舍生,成绩优异者,有机会被直接授予官职。我要争取的,
就是一个进入御史台的机会。”接下来的日子,林羽更加刻苦地学习。他不仅钻研经义,
更开始研究历代的律法和案例。他知道,作为一名言官,不仅要有勇气,更要有智慧。
他要让自己的每一句弹劾,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,切中李邦彦的要害。机会很快就来了。
御史台的一位监察御史因为年老致仕,出了一个空缺。按照惯例,
会从太学上舍生中选拔一人补缺。林羽凭借出色的成绩和在太学里的声望,
成功获得了这个名额。当他第一次穿上御史的官服,走进那座庄严肃穆的御史台大堂时,
心中感慨万千。他从一个现代的历史系研究生,到一个古代的破落书生,
再到如今手握监察大权的言官,这一路走来,充满了艰辛与挑战。但他知道,
这只是一个开始。他手中的这支笔,将不再是抄书的工具,而是捍卫家国的利剑。
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搜集李邦彦的罪证。他利用自己在市井间建立的关系网,
以及赵轩提供的军中情报,很快就掌握了李邦彦卖官鬻爵、贪污受贿、结党营私的大量证据。
他开始撰写他的第一份弹劾奏折。这份奏折,他将矛头直指李邦彦,罗列了其十大罪状,
字字泣血,句句铿锵。写完奏折后,林羽找到了赵轩,将奏折交给了他。“赵兄,这份奏折,
明日早朝,我会当庭呈上。李邦彦势力庞大,我此去,凶多吉少。若我遭遇不测,
请你务必将我的‘时务笔记’保管好,那里面有我对未来局势的判断,或许对你有用。
”赵轩接过奏折,手都在颤抖。他看着林羽那张平静的脸,心中充满了敬佩和担忧。“林兄,
你……你一定要小心!”林羽微微一笑,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放心吧。我既然敢做,
就有把握。为了这个国家,为了天下的百姓,我无所畏惧。
”---8 第7章 殿前惊雷## 第7章 殿前惊雷第二天早朝,气氛一如既往的沉闷。
文武百官分列两旁,听着宋徽宗点评着几幅新得的字画。李邦彦站在百官之首,
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,享受着皇帝的赞许。就在这时,
一个清亮的声音打破了这虚假的祥和:“臣,御史台监察御史林羽,有本奏!
”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年轻的言官身上。林羽身穿崭新的御史官服,身形笔挺,
眼神锐利,与周围的那些老成持重的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宋徽宗皱了皱眉头,
他并不认识这个年轻人。他有些不悦地说道:“讲。”林羽上前几步,高举手中的奏折,
朗声说道:“臣弹劾当朝宰相李邦彦,十大罪状!一,结党营私,排除异己;二,卖官鬻爵,
败坏朝纲;三,贪污受贿,中饱私囊;四,谄媚君上,蒙蔽圣听……”林羽的声音,
如同惊雷一般,在庄严的大殿里回响。他每念一条罪状,李邦彦的脸色就白一分。
当林羽念到第十条“私通外敌,意图不轨”时,李邦彦再也忍不住了。“一派胡言!
血口喷人!”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,对着宋徽宗哭喊道,“陛下,臣冤枉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