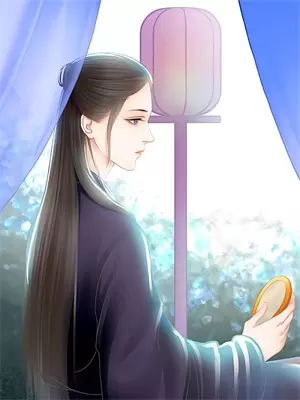我今年八十五岁,正在策划谋杀三个人。这件事我想了不是一天两天,是从三个月前,
那个下雨的下午开始的。那天,我在垃圾站翻瓶子,碰到了老孙。老孙以前跟我是一个厂的,
他扫厕所,我闺女彩华是坐办公室的文员。三十五年了,我从没放弃找过彩华,
见了以前厂里的老人就要拉住问几句。老孙看见我,眼神躲躲闪闪,想绕开走。我堵住他,
也不说话,就那么看着他。雨水顺着我脸上的褶子往下流,流进眼睛里,又涩又疼。
他最后叹了口气,把我拉到旁边的破棚子底下,递给我半瓶他喝剩的白酒,让我暖暖身子。
我没接,我只想知道我闺女在哪。“招娣啊……别找了。”他闷头灌了一口酒,
眼睛红得吓人,“彩华……她回不来了。”我胸口像被人狠狠砸了一拳,差点没站住。
三十五年,我跑断了腿,磨破了嘴,心里其实早就知道希望渺茫,可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,
还是像刀子一样。我抓住他干瘦的胳膊,指甲几乎掐进他肉里:“你看见她了?
她到底在哪儿?”老孙又灌了几口酒,好像那酒能给他壮胆。他凑近我,
嘴里的酒气混着臭味喷在我脸上,声音压得极低,
像鬼叫:“她……她被人害了……就在厂里,那年夏天,
说是加班那天……”接下来他说的话,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他说,那天晚上,
彩华被陈向东、赵大勇、王斌他们三个,骗回了空无一人的纺织车间。他们欺负了她,
三个畜生啊!我的彩华,我那爱干净、说话都细声细气的闺女!他们怕她出去告发,
坏了他们的前途,就……就用手,活活把她掐死了!老孙说,他那天晚上肚子不舒服,
半夜回厂里拿落在工具箱的药,正好撞见他们三个慌里慌张地从车间后门出来,
抬着一个用旧帆布裹着的长条东西,往那边正在打地基的新厂房工地跑。
他吓得躲在了废料堆后面,没敢出声。后来,他就听说彩华失踪了。
“地基……他们把她……埋进地基里了……”老孙说完这句,像被抽走了骨头,瘫坐在地上,
抱着头呜呜地哭,“我不是人……我怕啊……我没敢说……”我站在那里,浑身抖得像筛糠。
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、我的衣服,但我感觉不到冷,心里头有一把火在烧,
烧得我五脏六腑都疼。三十五年!我的彩华,就在离我家不到三里地的厂子下面,
冰冷的水泥地下面,躺了三十五年!而我这个当妈的,还像个傻子一样,满世界地找!
我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。那间到处漏雨的老房子,好像一瞬间也变得陌生了。
彩华小时候在这里蹦蹦跳跳的样子,好像还在眼前。她跟我说:“妈,等我发了工资,
给你买件新衣裳。”那衣裳,我等到头发白了,也没穿上。我不能让她就这么算了。
我去了派出所,把我这辈子知道的所有词儿都用上了,求他们重新查案。那个年轻的警察,
皱着眉头听我说完,翻了厚厚的本子,最后告诉我:“老太太,不是我们不帮你。
这案子时间太久了,都三十五年了,早就过了追诉期。而且,你说的这些,没证据啊,
光凭一个醉鬼的话,立不了案。”追诉期?我听不懂那么复杂的词儿。
我就问:“那我闺女就白死了?那些杀千刀的,就能逍遥法外了?”警察叹了口气,
眼神里有点同情,但更多的是无奈:“法律是这么规定的。大娘,您……节哀吧。”节哀?
我哀了三十五年,眼泪早就流干了。现在,我心里只剩下恨。从派出所出来,我没回家。
我鬼使神差地,走到了镇上最热闹的那条街。我打听了一圈,指着名字问。结果,
真让我问着了。陈向东,开了家大纺织公司,叫什么“向东集团”,是县里的名人,
人大代表,有钱有势,住在河那边新盖的别墅区里。赵大勇,退休了,以前是厂里的技工,
现在住在儿子家,帮着带孙子,日子过得挺安稳。王斌,也是个老酒鬼,
住在城北那片快要拆迁的破房子里,听说身体也不太好了,但还活着。他们都活着,
活得人模狗样!我的彩华呢?我的彩华在地下,连副骨头都找不回来!那天晚上,
我坐在吱呀作响的破床上,看着墙上彩华唯一的一张照片,那还是她刚进厂时照的,
笑得像朵花。我看着看着,就伸出手,用指头摸了摸她的笑脸。“彩华,”我对着照片说,
声音哑得我自己都陌生,“妈没本事,法律不给你做主了。”我摸出白天捡烟盒时,
一起捡来的半截铅笔头。又从那堆废纸里,翻出一张稍微硬实点的烟盒纸,
把它在膝盖上慢慢摊平。我的手抖得厉害,不是因为老,是因为恨。我一笔一划,
用尽全身的力气,在那张皱巴巴的烟盒纸背面,
写下了三个名字:陈向东 赵大勇 王斌字写得歪歪扭扭,像爬虫,但很清楚。我把这张纸,
看了又看,然后小心翼翼地折起来,塞进了我贴身的衣服口袋里,挨着我的心口放好。那里,
心跳得很慢,很沉,像在敲鼓。好了,这就是我的清单。我要做的事,都在这张纸上了。
我今年八十五岁了,土埋到脖子的人。我没钱,没势,没力气,
走到哪儿都被人当成糊涂、没用的老废物。但现在,这好像成了我唯一的机会。
没人会防备一个路都走不稳的老太太。我把那张写着三个名字的烟盒纸,当成了我的命。
每天贴身藏着,睡觉都摸着。我知道,光有恨不行,得有计划。我一个快入土的老太婆,
怎么弄死三个大男人?得用脑子。我先从赵大勇开始。他离我最近,住在他儿子家那个小区。
我跟我那总爱打听别人家事的邻居说,医生让我多走动,腿脚才能利索。从那天起,
我天天“散步”就散到赵大勇他家楼下。我不靠近,就找个能看见他家楼道的马路牙子坐着,
手里拿个破编织袋,假装是捡累了歇歇脚。我一坐就是大半天,眯着眼睛,像只打盹的老猫。
没人会注意一个发呆的老太太。我看着他儿子儿媳几点出门上班,
看着他孙子几点被送去上学,看着赵大勇自己几点出来溜达,去哪个菜市场,
爱在哪儿跟人下棋。我还“顺便”翻翻他们楼下的垃圾桶。赵大勇家的垃圾里有好多药盒子,
都是治高血压的。我记住了。看了差不多一个月,我心里有数了。赵大勇身子骨还算硬朗,
但有个毛病,信佛信得厉害,特别怕报应。每月农历十五,
他都要一个人走去郊区那个小破庙烧香,雷打不动。去庙里有段路,很偏,没摄像头,
路边还有个小陡坡。时候到了。那天是十五,晚上天擦黑。我用捡来的、不记名的旧手机卡,
给他发了一条早就编好的短信,字不多:“三十五年前,纺织厂车间,李彩华看着你呢。
冤有头,债有主。”发完,我就把卡掰断,扔进了河里。然后我慢慢走到那段偏僻的路附近,
躲在草丛后面。我等了没多久,就看见赵大勇慌里慌张地从庙那边过来,脚步都有点飘,
一边走一边四下看,好像后面有鬼撵他。我提前在路当中,
倒了些从修车铺后面偷摸弄来的黑机油。他心神不宁,根本没看脚下,一脚踩上去,
哎哟一声,整个人猛地向后一滑,后脑勺“咚”一下,狠狠磕在路边的水泥台子上,
连声都没吭,就不动了。我远远看着,等了几分钟,确认他没动静了,才慢慢转身离开。
心口跳得厉害,但不是怕,是另一种感觉,像憋了三十五年的那口气,终于吐出来一点点。
第二天,我听小区里议论,说老赵头晚上摔死了,真倒霉。警察来了,看了现场,说是意外。
我坐在老地方,继续晒太阳,没人多看我一眼。晚上回家,我掏出那张烟盒纸,用铅笔头,
在“赵大勇”三个字上,重重地划了一道杠。第一个。收拾了赵大勇,我盯上了王斌。
他是个酒鬼,住在城北那片要拆的破房子里,没啥亲人。这更容易。
我摸清了他常去打散装白酒的那家小店。店主是个马虎人,舀酒的那个公用水瓢,
用完就随便往水桶里一涮,桶里的水半天都不换。我手里有药。是我平时捡废品时,
特意留意捡来的别人吃剩扔掉的降压药,我一片片收集起来,在家用石头碾成了细细的粉末,
用纸包着。我连续三天,趁店主转身招呼别的客人,或者去里屋拿东西的时候,
飞快地把一点药粉抖进那个水瓢里,再晃一晃。量不多,但架不住王斌天天喝,顿顿喝。
没过一个星期,就传出消息,王斌喝酒喝死了,说是脑溢血。警察又来了,看了看,
闻着满屋子酒气,摇了摇头,也没说啥。那天晚上,我在“王斌”的名字上,划了第二道杠。
两个了。我以为我能悄悄地把最后一个也收拾掉。但我低估了陈向东。
赵大勇和王斌接连死了,还都跟当年的事有关联,陈向东这种比狐狸还精的人,
不可能不怀疑。他比那俩加起来都难对付。他先是让社区的人来找我。主任带着人,
提着油和米,说是慰问空巢老人。嘴上说得好听,问我最近身体咋样,有啥困难,
眼睛却在我这破屋子里到处瞟。主任说:“刘奶奶,您一个人住这我们不放心啊,要不,
我们帮您联系个养老院?环境好,还有人照顾。”我心里跟明镜似的,这是想把我关起来,
不让我在外面“溜达”了。我立刻装糊涂,拉着主任的手,
眼泪说下来就下来:“不去不去……我哪儿也不去,我等我闺女回来呢……她叫彩华,
在纺织厂上班,你见过她没有啊?”主任一脸尴尬,安慰了我几句,赶紧走了。这招不行,
陈向东又来硬的。一天晚上,我捡完废品往回走,两个流里流气的小年轻堵住我,
一把抢过我的编织袋,把里面的瓶子罐子倒了一地。“老不死的,捡得很欢实啊?
”一个黄毛推了我一把,我踉跄一下,差点摔倒。“有人让我们给你带个话,安分点!
别他妈瞎打听,不然下次,打断你的老骨头!”我知道这是陈向东派来的。我没吭声,
等他们说完,准备走的时候,我猛地往地上一躺,扯着嗓子喊起来:“打人啦!抢劫啊!
欺负老人啊!救命啊!”我嗓门大,又是晚上,很快就有人开窗看,还有几个路人围了过来。
那两个小混混没想到我来这招,脸都白了,骂骂咧咧地赶紧跑了。我自己从地上爬起来,
拍拍土,在周围人同情的目光里,慢慢收拾我的废品。我知道,陈向东不敢真把我怎么样,
他怕把我逼急了,我会不管不顾地去闹。最恶心的是,陈向东他自己来了。他开着小轿车,
穿着笔挺的西装,还带着记者模样的人,在我们社区干部面前,演了一出大戏。
他紧紧握住我的手,一脸悲痛:“刘妈妈,我知道您心里苦。赵大勇和王斌都走了,
过去的错,就让它过去吧!您要向前看,彩华妹子在天之灵,
也肯定不希望您一辈子活在仇恨里,您说是不是?”他话说得漂亮,手上却在使劲,
捏得我手骨生疼。他那眼神,看着像是在关心我,其实里面全是冰碴子和警告。
我看着他虚伪的嘴脸,胃里一阵翻腾。但我没甩开他,反而顺着他的话,呜呜地哭起来,
演得比他还像:“陈老板是好人啊……总来看我……可我老婆子命苦啊……我闺女没了,
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……”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,社区干部赶紧来劝。
陈向东脸上的笑有点僵,他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。他走了之后,我知道,
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陈向东现在像只受了惊的王八,把头缩在硬壳里,我找不到下嘴的地方。
他住的是有保安看守的别墅,出门坐车,身边可能还跟着人。我靠近不了他。我坐在家里,
看着清单上最后一个名字“陈向东”。前面两个名字都被黑杠划掉了,像两道深深的伤口。
就剩他一个,孤零零地立在那里,嘲笑着我。硬的不行,骗的不行。我得找到他的死穴。
死穴……我猛地想起了老孙的话。他说,赵大勇有写日记的毛病,干了啥亏心事都往上面写,
说这样能镇住邪气,让自己心安。那本日记!那里面,一定记着三十五年前那天晚上,
他们干的畜生事!那才是能真正钉死陈向东的东西!赵大勇死了,
他儿子媳妇正在处理他的遗物。我看到他们在楼下烧旧衣服、旧书本。我的心,
一下子热了起来。好像,又有路可以走了。我盯上了赵大勇的儿子一家。
他们正在处理赵大勇的遗物,好些旧东西就直接扔在楼下的垃圾堆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