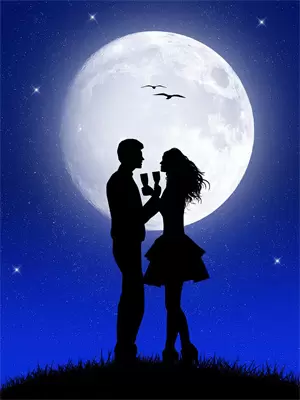简历崔以恒又迟到了。 当他推开会议室的门时,十几双眼睛几乎在同一秒里抬起头,
表情里混着尊敬、戒备和一点点幸灾乐祸。 他依旧那副温和的笑,
像是对所有情绪都心知肚明——只是不打算回应。墙上的投影正停在一页简历上,
标题是“院长候选人简介”。那份简历不是他的,
可在场的人都清楚:如果没有去年的那封匿名举报信,屏幕上现在就该是他的照片。
他慢慢坐下,笔挺的衬衫袖口闪着微光。有人递来茶水,他轻声道谢。 会议继续进行,
台上那位年轻副教授在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,语速飞快,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影响因子。
崔以恒低头,轻轻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字母——“IF=幻觉”。他从不缺乏幽默感,
只是别人听不见。崔以恒的履历干净得像一张抛光过的钢板。学历、论文、项目、奖励,
全在正确的位置上闪闪发亮。
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台电脑、一台打印机和一张永远空着的访客椅。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,
封面写着四个字:“科研人生”。 那是他学生送的生日礼物,第二页就写着:“导师,
愿您永远被引用。”他确实被引用过无数次——不仅在论文里,也在传言里。
在学院的走廊上,学生们提到他时,语气里常带着一种复杂的崇敬。“崔老师不一样,
”他们说,“他是真正懂怎么写的人。” 他们指的“写”,当然不是写情书。
他在学术圈的声誉建立在一种近乎机械的精确上。别人写论文是劳动,他写论文像呼吸。
他能在航班上、会议间、甚至做核酸排队时修改摘要。他的文稿干净得像手术刀,
句式锋利、结论漂亮,让审稿人没机会插手。有学生说他像个“论文工厂”。
崔教授笑了笑:“工厂也需要灵魂,只不过是标准化的灵魂。”他的第一任妻子在海外,
一直留在那里。两人分开得体,没有争执,没有戏剧性。她说:“我们都太忙了。
” 崔以恒答:“忙是文明的形式。”他们的儿子偶尔视频,
他总在屏幕那端看见父亲的额头、眼镜反光,还有那张总在电脑前的脸。 后来,
连视频也少了。崔教授习惯了孤独,也开始相信孤独能提高科研效率。
那封举报信出现在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刻。“崔以恒教授与女研究生关系不当,
存在违反师德行为。” 信件不长,逻辑严密,用词克制,
甚至引用了《教师职业准则》第四条。 像是某篇伦理学论文的摘要。学院调查时,
他没表现出慌乱,只问了一句:“请问,这算内部评审还是外审?
” 负责调查的主任尴尬地咳了两声。几周后,结果是“证据不足,无法定性”。
事情似乎过去了。但从那以后,他的上升通道也悄然关闭。崔以恒自己倒显得平静。
“做学术,本来就不该分心。” 他说这话时,语气温柔得像是在安慰别人。
他第一次再婚是在那年年底。 对象是自己带过的女博士,三十岁出头,
聪明、听话、情绪稳定。没有举办婚礼,也没请同事。
他们的结合更像是一个合作项目:目标清晰、周期两年、成果可预期。 两年后,
女方升了副教授,他们平静离婚。外界唯一的线索,是女方那篇署着他名字的论文,
后来被引用了上百次。崔教授没有多解释,只说了一句:“合作结束而已。
” 那句话后来被流传成一种学术名言,甚至被学生印在实验室的纪念T恤上。此后的几年,
感轨迹像一张更新日志: 第二次婚姻、第三次、第四次……每一段都伴随着新的科研成果。
他仿佛拥有某种神秘的统计规律:与他共事的女性,
平均在两年内就能拿到职称;而他自己,也从不缺下一个“研究对象”。校内有流言,
说他是“学术配对系统的活广告”。 有人羡慕,有人鄙夷,但没人否认他的实力。 毕竟,
他从不藏私。他会帮人改基金、审论文、写推荐信,语气始终礼貌克制,
从不越界——至少在文字上。他的学生们渐渐学会模仿他的说话方式。
那是一种去掉情绪的语言,精准、稳重、无菌。 在这样的语气里,任何暧昧都显得合理。
有时候,崔以恒自己也分不清,他究竟是在研究人,还是在研究自己。 深夜的办公室,
他常打开那份“个人简历”。 文件名是:“CV_Final_Updated”。
他反复修改,添加新的成果、合作、指导学生、项目奖励。每一行都像一层保护壳,
让他更安全,也更孤独。他知道,
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符号—— 一个代表成功、效率、控制的符号。 有时候,
他甚至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,就是让别人相信:这种生活仍然值得。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,
他轻声念出简历上的最后一行: “主要研究方向:人类行为与复杂系统。”他笑了一下。
那的确没写错。
举报信那封举报信最初是被打印出来的。 放在院长办公室的文件夹里,
夹在两份会议纪要之间。 没人知道是谁放进去的,也没人承认看过。 可第二天上午,
它已经成了整栋教学楼里流传最快的文本。信只有两页,纸张厚实,打印字体是宋体四号,
页脚有页码,排版整齐得像年度考核报告。 开头一句话:“我谨以学院成员的身份,
反映崔以恒教授在师生关系上的严重不当行为。
”然后是一连串编号:1、2、3……像是实验步骤。 每一条都简洁、有条理,
还配有时间与地点。甚至在末尾附了几段“补充说明”,引用了“教育部师德文件”的条款。
信的末尾没有署名,
只有一个邮箱地址:academic_truth@……读起来不像情绪性的控诉,
更像一篇“研究报告”。 这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不安。院长在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,
用了一个模糊的词:“反映”。 “有同志反映,
崔老师最近的科研工作中可能存在……一些需要澄清的个人问题。”会议室的空气瞬间紧了。
所有人都低头翻文件,仿佛在认真阅读,其实是在避免视线相遇。崔以恒听完,点了点头。
他没有表现出惊讶,只是拿起笔,在会议记录的空白处写下三个字:“非匿名”。
那是他的条件。 他习惯对一切质疑要求来源、引用、样本量。院长咳了一声,
略带歉意地说:“这个……举报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。” “那就很难讨论。
” 崔教授微笑着回答,语气像在谈审稿意见。会议就这样结束了。没人敢再提那封信。
调查还是启动了。 调查组三个人:院党委书记、人事处代表、学院副院长。
他们约崔以恒谈话的那天下午,天气闷热,办公室的空调嗡嗡作响。
书记先开口:“崔老师,我们只是例行了解情况,请您配合。”崔教授点头:“当然。
您需要我提供什么?邮件记录,还是实验室出勤表?” 那语气里听不出紧张,
反而像在准备一场公开答辩。
书记有些尴尬:“举报信提到您和一位女研究生关系比较密切……她姓林。
” 崔以恒想了想:“林?哦,她。论文写得不错。最近刚中了一篇顶刊。
”“举报人说你们在校外见过多次,还一同出差。” “那次会议她做口头报告,
我是通讯作者。报销走公账,行程可查。
”“那您能解释为什么有两位老师看到您晚上一起吃饭?” “学术指导需要讨论数据。
晚饭时思路更清晰。科学研究不分昼夜。”三人面面相觑。书记叹了口气,
合上笔记本:“我们了解了。”整个谈话持续不到十五分钟。 崔以恒走出办公室时,
神情一如平常。 他顺手掸了掸袖口的灰尘,仿佛刚做完一次普通的会议汇报。
接下来的一个月,他的课照常上,学生照常围着他讨论实验。 只是偶尔在走廊里,
谈话的声音会在他靠近时停下来。 他假装没听见。 那种寂静,
他很熟悉——像审稿系统里被退回的稿件,没有意见,
只有“Decision: Reject”。他开始更频繁地工作。
每天早晨七点半到办公室,夜里十二点离开。 学生们以为那是某种“精神力量”,
只有他自己知道,那其实是一种“声音替代”。 在敲键盘的声音里,流言显得不那么清晰。
有一天,他去科研处开会,路过复印机室,看见有人在复印一叠文件。
那叠纸上隐约有他的名字。 他走近一步,那位职员慌忙合上机器,说:“哦,
这个……领导要的备份。” 他笑笑:“辛苦了。” 语气温和,没有一点责怪。可那晚,
他梦见自己被一页页复印出来。 影印机的灯条一遍又一遍扫过,他的脸在白纸上越来越淡,
最后只剩名字。 醒来时,他的手仍在空气里比划着签字动作。一个月后,调查结束。
结果公布在学院内部邮件:“经核实,未发现实质证据,举报情况无法成立。
望全体教职工引以为戒,注意师德形象。”语气官样、模糊,却像一块石头,轻轻落地。
学院的空气又恢复平静。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,只是时间又向前挪了一点。
崔以恒看到邮件那天,刚好在改一篇基金申请书。 他读完通知,
删掉了正文里一句原本写着的“本项目有望实现科研伦理的规范化建设”。
他觉得那句话太多余。几天后,他收到了林同学的邮件。 内容很短:“老师,对不起,
可能是我……让人误会了。”他没有回。
只是把邮件移到了一个名为“旧项目”的文件夹里。
他从不删除文件——删除意味着承认。保存,才是一种更高级的遗忘。新的学期开始了。
崔以恒依旧在讲“科研写作”课。
课堂上他让学生做一个练习: “假设你是一名审稿人,请修改以下段落,
使其逻辑更严谨。” 屏幕上那段话是:“由于信息不对称,个体之间的信任难以建立,
导致研究过程陷入长期的不确定性。”学生们埋头修改。 崔教授背着手,
在讲台上来回走动。 窗外阳光刺眼,他的影子在讲桌上缓缓移动。 他忽然意识到,
这句话的确写得太真实了。那天晚上,他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。
校园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,树影斑驳,风吹过旗杆发出细微的嗡鸣。
他突然想起那封举报信——纸质的,整齐的,理性的。
它甚至像极了他自己曾经写过的文字。 冷静、精确、没有情绪。他停下脚步,想了想,
忽然有种荒诞的念头: 也许那封信,是他自己写的。 或者,
至少是那个他早已丢弃的版本。他笑了笑。 风把笑声吹散,像吹散一张打印纸的灰。
第二天,他换上西装,去参加学院年度评审。 签到表上,
他的名字后面多了一个括号——“未定级”。 他盯着那两个字几秒钟,签了字。
字体依然端正,没有抖。签完,他把笔帽扣好。 那动作缓慢、安静,
像一个人刚刚关掉了什么—— 比如一扇门,一封信,或者,某种久已存在的信念。
再婚公式崔以恒的第二次婚礼很小。 没有婚纱、没有誓言、也没有宴席。 只有一张合影,
拍在一面暗蓝色的背景前。新娘微笑,他微笑,摄影师说:“好了,下一个。
”照片后来被放在他的书架上,夹在两本英文专著之间。
那笑容与封面的字体一样——专业、可引用、无情绪。新娘名叫陈潇。
崔以恒不是她的博士导师去帮助过她。 她的论文题目很长,结论冗余,
但他帮她压缩到了九千字。 那一年,她的文章被某国际期刊录用;那一年,他们结婚了。
学生们说:“崔老师真会提携人。” 没人敢用别的词。婚后的生活平静得近乎无声。
他们共用一间书房,书桌并排放着。晚上十点以后,她改文,他改基金。
偶尔他伸手去拿订书机,她会稍稍让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