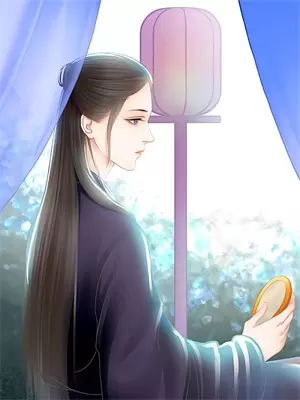奶奶的包裹到付后收到奶奶遗物那天,我莫名在客厅里转了三圈磕了个头。
闺蜜尖叫着说我磕头的姿势和纸扎人一模一样。 深夜,衣柜里传来奶奶的呼唤:“囡囡,
来穿嫁衣。” 我颤抖着打开衣柜,里面赫然躺着奶奶缝的红色嫁衣。 而试衣镜里,
映不出我的脸。---1 诡异包裹快递员把那个沉甸甸的包裹递过来时,
林晚就觉得脖子后面一阵发凉,像是有人贴着皮肤吹了一口气。包裹是到付的,运费不便宜。
她签收时,指尖触到粗糙的纸壳,一种难以言喻的黏腻感挥之不去,
仿佛沾上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寄件人信息模糊,只勉强能辨认出“南坪镇”几个字。
她老家就在那儿,一个地图上都难找的小地方。可老家早就没人了,
最后一个亲人——她的奶奶,半个月前刚刚过世。她回去操办了丧礼,这才回城没几天。
谁寄来的?她把包裹放在客厅茶几上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心里有点发毛,不想拆。
也许是奶奶的某个老邻居整理的遗物吧,她这么安慰自己。转身想去倒杯水,左脚刚迈出去,
右脚却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绊了一下,身体一个趔趄,不受控制地原地转了个圈。
她稳住心神,觉得莫名其妙,可脚步却没停,又接连转了兩圈,动作僵硬得不像她自己。
第三圈转完,面朝客厅空荡荡的东墙,她的膝盖猛地一软,“噗通”一声就跪了下去,
额头结结实实地磕在了冰凉的瓷砖地板上。“咚!”一声脆响,震得她脑仁发懵。“小晚!
你干什么呢!”恰巧来给她送落下的文件的闺蜜周婷,站在玄关,目瞪口呆地看着她,
脸上血色褪尽,连声音都变了调。林晚茫然地抬起头,额角一阵刺痛,肯定红了。
周婷冲过来,却没第一时间扶她,而是指着她,手指抖得厉害,
声音发颤:“你…你刚才…磕头的样子…我的天…”“我怎么了?”林晚被她吓住了,
撑着地面想站起来,浑身却使不上劲。“像…像那些给死人烧的纸扎人!就是童男童女那种,
关节硬邦邦的,转起来,磕下去…一模一样!”周婷的声音带着哭腔,眼里满是惊恐,
“小晚,你别吓我啊!”林晚的心猛地沉了下去,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头顶。纸扎人?
她想起奶奶丧礼上,那些堆在灵堂角落,色彩鲜艳,面容呆滞,透着森森鬼气的纸人。
她怎么会…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回那个还没拆封的包裹上。是它吗?自从它进了这个门,
一切都变得不对劲了。2 邪门遗物那个包裹最后还是拆了。里面是几件奶奶生前常穿的,
洗得发白的旧衣服,一股樟脑丸和老人身上特有的、混合着草药和淡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衣服下面,压着一个小木匣子,打开一看,林晚和周婷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里面是些零碎的老物件,最扎眼的,是几缕用红绳紧紧捆着的头发,细细软软,
看起来像是小孩子的。还有几颗掉了漆的彩色纽扣,半截干枯发黑的小指甲。
“这…这都是什么啊…”周婷声音发紧。林晚胃里一阵翻腾。她认得那头发,奶奶说过,
那是她三岁前剃下来的“胎毛”,本该早就扔掉的,怎么会…还有那指甲?木匣最底层,
是一张折叠起来的、泛黄脆硬的毛边纸。上面用某种暗红色的颜料,
画着一些完全看不懂的扭曲符号,像是字,又像是某种抽象的图案,看得人头晕眼花。
“邪门…太邪门了…”周婷一把抓住林晚的胳膊,“小晚,这东西不能留,赶紧扔了!
”林晚何尝不想扔?可手指碰到那些冰凉的物件,尤其是那几缕属于她自己的胎毛时,
一种奇异的感觉攫住了她——这些东西,和她有着斩不断的联系,扔不掉,或者说,不敢扔。
她最终还是没扔,只是把木匣子塞回了包裹,连同那些旧衣服,
一股脑地塞进了客厅角落那个闲置的衣柜最底层,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份不安也一并封存。
夜里,林晚睡得极不安稳。迷迷糊糊中,好像听到有人在哭,细细的,抽抽噎噎,
是个小孩的声音。又好像听到奶奶在哼唱那首古老的、不成调的歌谣,声音苍老而沙哑,
断断续续,听不真切。“……囡囡乖……穿红衣……”她猛地惊醒,冷汗已经浸湿了睡衣。
窗外月色惨白,透过窗帘缝隙,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冷光。屋子里静得可怕。然而,
那声音并没有消失。它不是来自梦境,而是真真切切地,从卧室墙边那个衣柜里传出来。
窸窸窣窣……像是有人在用指甲轻轻刮挠着柜门内侧。然后,一个她熟悉到骨子里,
此刻却让她浑身血液都快冻结的声音,幽幽地响了起来,
带着老年人特有的、黏连的气音:“囡囡……来……来穿嫁衣……”是奶奶的声音!
林晚瞬间僵直,心脏狂跳得几乎要撞碎胸骨。她死死咬住嘴唇,不敢发出一点声音,
整个人缩进被子里,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。那呼唤声停了片刻,就在她以为只是噩梦一场时,
衣柜里又传来了新的动静——是布料摩擦的声音,很缓慢,
像是在抖开一件存放了很久的衣服。
“囡囡……奶奶给你……缝好了……红色的……好看……”林晚崩溃了,
一把抓过床头柜上的手机,哆嗦着拨通了周婷的电话。
“婷婷……它…它在叫我……衣柜…奶奶在衣柜里……”她语无伦次,
眼泪混着冷汗流进嘴里,又咸又涩。电话那头的周婷显然也吓坏了,但还算镇定:“别怕!
小晚你别怕!我…我马上过来!你等着我!”3 衣柜惊魂周婷来得很快,
几乎是踹门进来的。她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在楼下便利店买的剪刀,也不知道是防身还是壮胆。
一进卧室,看到林晚惨白如纸、缩在床角瑟瑟发抖的样子,周婷的眼圈就红了。
她打开房间里所有能打开的灯,明晃晃的灯光驱散了些许阴影,
却驱不散那股盘踞在空气中的阴冷。衣柜静静地立在墙边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“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听错了?”周婷咽了口唾沫,声音干涩。林晚疯狂摇头,
手指死死攥着被角,指节泛白:“没有!她叫我!她让我穿嫁衣!”周婷深吸一口气,
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她走到衣柜前,犹豫了一下,猛地伸手,
拉开了柜门——里面挂着几件林晚平时穿的外套,下层叠放着一些毛衣、裤子。
看上去一切正常。“你看,没事……”周婷的话还没说完,声音就卡在了喉咙里。
她的目光定格在衣柜最底层,那堆原本叠放着的毛衣旁边。那里,不知何时,
多出了一抹极其刺眼的红色。林晚也看到了。那不是她任何一件衣服。周婷颤抖着手,
将那抹红色扯了出来。是一件嫁衣。一件老式的、手工缝制的红色嫁衣。布料是某种丝绸,
红得像是用鲜血染过,上面用金线绣着繁复的鸳鸯石榴图案,那刺绣的针脚细密得惊人,
也……熟悉得惊人。林晚认得,那是奶奶的针线活儿!嫁衣展开,
一股更浓烈的、混合着霉味和奇异腥气的味道弥漫开来。它保存得并不好,
某些地方甚至能看到深色的、硬邦邦的污渍。
“这……这东西什么时候……”周婷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林晚死死盯着那件嫁衣,
心脏一下一下沉重地撞击着胸腔。她记得,奶奶去世前那段时间,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,
神神秘秘地缝制着什么,不许她看。难道……就是这件?可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
她明明亲手把包裹塞进了客厅的衣柜!“扔了它!快扔了它!”周婷像是被烫到一样,
把嫁衣扔在地上,拉起林晚就想往外跑。林晚却像是被钉在了床上,
目光无法从地上那摊刺目的红色上移开。一股莫名的力量,或者说,
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带来的顺从,驱使着她。她下了床,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,
一步步走向那件嫁衣。“小晚!你干什么!”周婷惊恐地想拉住她。林晚甩开了她的手,
眼神空洞。她弯腰,捡起了那件冰凉滑腻的嫁衣。布料入手,
一种难以形容的阴冷顺着指尖迅速蔓延到全身。鬼使神差地,她抱着嫁衣,
走向卧室门边那个等身高的试衣镜。
她想看看……自己穿上它……会是什么样子……她站定在镜前。镜子里,
清晰地映照出她身后惊慌失措的周婷,映照出卧室的布局,映照出头顶明亮的吸顶灯。唯独,
没有映出她自己的脸。镜子里面,她站立的位置,空空如也。
只有那件被她抱在怀里的、血红色的嫁衣,诡异地悬浮在半空中。林晚的呼吸骤然停止。
她僵硬地,极其缓慢地抬起一只手,摸了摸自己的脸颊。触感温热,皮肤下有血液在流动。
可镜子里,那只手并不存在。镜面光滑冰冷,只倒映着现实,却抹去了她的影像。“啊——!
!!!!”周婷的尖叫声,和她自己内心深处无声的崩溃,同时炸开。
4 诅咒轮回接下来的几天,林晚活得像个游魂。她不敢再照任何能反光的东西,
窗户、玻璃、甚至手机黑屏。她和周婷试过把那件嫁衣扔掉,撕碎,甚至想烧掉。
可无论她们把它丢进楼下的垃圾桶,还是塞进远处的垃圾转运站,第二天清晨,
它总会完好无损地、静静地重新出现在那个衣柜里。用剪刀去剪,刀刃崩了口子,
布料却毫发无伤。打火机的火苗靠近,会莫名熄灭,连一点焦痕都留不下。它赖上她了。
奶奶的呼唤声,也不再局限于深夜。有时是黄昏,有时甚至是正午阳光最烈的时候,
那苍老、阴森的声音会毫无预兆地响起,从衣柜,从床底,从任何一个阴暗的角落钻出来,
萦绕在她耳边。
“囡囡……时辰快到了……”“穿上……穿上就好了……”林晚迅速憔悴下去,眼窝深陷,
眼下是浓重的青黑。她开始出现幻觉,总觉得身边跟着一个看不见的小女孩,
穿着红色的旧衣服,低着头,轻声啜泣。夜里,那小孩的哭声和奶奶的呼唤交织在一起,
几乎要把她逼疯。周婷请来了据说很厉害的大师,大师在家里转了一圈,脸色大变,
连钱都没收就匆匆走了,只留下一句:“怨气太重,缠得太深,管不了,
你们……自求多福吧。”唯一的线索,是周婷翻遍了那个木匣子,
在夹层里找到的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类似那件红嫁衣的年轻女子,
低着头,看不清面容,背景似乎是个古老的祠堂。照片背面,
用褪色的墨水写着一个日期:癸亥年腊月初七。林晚查了万年历,对应的是1983年。
那一年,奶奶还年轻。而腊月初七,据她所知,
是老家一个早已废止的、名为“祀娘”的诡异习俗的日子。
她小时候似乎听奶奶含糊地提过一嘴,说是很久以前,镇里会选八字特殊的女孩,
在特定的年份穿上特制的嫁衣,完成某种仪式,以祈求宗族安宁。但具体的,奶奶从不细说,
只说那是“旧社会的糟粕”。难道……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中成型。
她不是唯一的“囡囡”。在她之前,早有别的女孩,被迫穿上了这身血红?
5 血债真相林晚决定回南坪镇。她必须回去,回到一切的起点,也许只有在那里,
才能找到解开这恐怖诅咒的方法。周婷不放心,执意要跟她一起去。
老家那栋阴暗潮湿的老宅,比记忆中更加破败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
一股陈年的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。她们直接去了奶奶生前居住的房间。
在奶奶那个老式雕花木床的床板背面,林晚摸到了一个暗格。费劲打开后,
里面放着一本边缘破损的牛皮笔记本。笔记本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,
上面是奶奶略显潦草的笔迹。里面断断续续记录了一些事情,
夹杂着一些类似木匣里那种扭曲的符号。“……又快到轮替之年了。癸亥年,属猪,
阴月阴日生的囡囡……这次,轮到我们林家了。”“……阿萍不愿意,哭了一夜。
可有什么办法?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,是为了全镇的人……得罪了‘祀娘’,
是要降灾的……”“……嫁衣改好了,用的是祖传下来的料子,浸过血,绣了符……穿上它,
去祠堂后面那个废弃的院子,
算礼成了……”“……阿萍走了……穿着那身衣服……他们都说她去了好地方……可我知道,
她恨……她肯定会恨……”笔记在这里中断了几页,后面再提起,笔迹变得更加颤抖、混乱。
癸亥年……轮到我的晚晚了……不行……绝对不行……我得做点什么……”笔记的最后几页,
画满了更加复杂扭曲的符咒,像是奶奶在尝试某种对抗的方法。最后一页,
只有用几乎戳破纸背的力度写下的一行字:“错了!全都错了!那不是庇佑!是诅咒!
穿着红嫁衣死在镜前的,没有一个能往生!它们都被困住了!一个个,一代代!
”林晚和周婷看完,遍体生寒。原来,所谓的“祀娘”,
根本就是一个延续了不知多少代的恶毒诅咒!一个用特定八字女孩的性命和灵魂,
去满足某个邪祟的恐怖轮回!而奶奶,似乎是想保护她,
才留下了那个木匣和那些诡异的东西,试图做些什么,却显然……失败了。甚至可能,
她的尝试,反而提前触发了什么。“走!快离开这儿!”周婷拉起林晚就想跑。就在这时,
老宅里的温度骤然降低,光线也迅速暗了下来,仿佛一瞬间从白天跳到了黑夜。
“嘻嘻……”一声清晰的小女孩的轻笑,在死寂的房间里响起。两人猛地回头。
只见房间角落那个蒙尘的穿衣镜前,不知何时,
多了一个模糊的、穿着红色旧衣服的小小身影,背对着她们,低着头。而那面蒙尘的镜子里,
映出的,却不是那个小女孩的背影。镜面如水波般荡漾,里面浮现出的影像,是林晚!
镜中的林晚,穿着一身血红色的嫁衣,头上盖着红盖头,
静静地站在一个类似古老祠堂的房间里。她的身边,影影绰绰,
似乎还站着好几个同样穿着红嫁衣、盖着盖头的女子身影,高低胖瘦各不相同。
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,像是一排等待了许久的……新娘。与此同时,
那件被林晚塞在背包最底层、以为暂时摆脱了的血红嫁衣,竟无声无息地,
再次出现在了她的身上!那冰凉的丝绸触感紧贴着皮肤,上面的金线刺绣仿佛活了过来,
微微蠕动。奶奶那幽怨、急切的呼唤声,从四面八方涌来,不再是单一的来源,
而是无数个苍老、阴森的声音重叠在一起,疯狂地钻进她的脑海:“囡囡——!
”“时辰到了——!”“穿好嫁衣——!”“入镜——!”林晚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,
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、冰冷的力量攫住了她的四肢,强迫着她,一步一步,
僵硬地朝着那面浮现着恐怖景象的镜子走去。周婷哭喊着死死抱住她的腰:“小晚!
不要过去!不要看镜子!”可那力量太大了。林晚的脚根本不受控制,
指甲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音。她能感觉到,背包里那个小木匣在发烫,那几缕她的胎毛,
仿佛燃烧了起来。镜面越来越近,里面那个盖着红盖头的“她”,似乎动了一下,缓缓地,
抬起了手,做出了一个“来”的手势。阴风呼啸,卷起地上的尘埃,
老宅里仿佛有无数个声音在同时哭泣、嘻笑、吟唱。
就在林晚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那冰冷镜面的刹那——“砰!”一声巨响,
老宅那本就不甚牢固的大门,被人从外面猛地撞开了。一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柱刺破昏暗,
精准地打在了那面诡异的镜子上。镜面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水面,剧烈地扭曲起来,
里面的红嫁衣影像瞬间模糊、溃散!那束缚着林晚的冰冷力量骤然一松,
她和死死抱着她的周婷一起,狼狈地摔倒在地。手电光后,一个佝偻的身影站在门口逆光处,
看不清面容,只能听到一个苍老而沙哑,
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声音低吼道:“哪个叫你们动‘祀娘’的东西的!不想活了?!
”6 镜中新娘手电光剧烈晃动,将门口那佝偻身影拉得忽长忽短,如同扭曲的鬼影。
林晚和周婷惊魂未定地瘫坐在地上,大口喘着气,冷汗浸透了后背。
那件强行出现在林晚身上的血红嫁衣,在强光照射和那声怒吼后,竟如同褪色的幻影般,
迅速变得透明、稀薄,最终彻底从她身上消失,只留下皮肤上仿佛被冰棱划过的刺骨寒意。
门口的身影走了进来,手电光略微放低,照亮了他自己。是个干瘦的老头,脸上沟壑纵横,
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,眼神浑浊却锐利,像鹰隼一样扫过房间,
最后定格在那面已经恢复正常的蒙尘镜子上,眉头死死拧紧。“三……三叔公?
”林晚认出了来人。这是镇上的老辈人,据说年轻时走过江湖,懂些旁门左道,脾气古怪,
常年守着镇子边缘那座几乎被人遗忘的旧祠堂,很少与人来往。奶奶在世时,
似乎和他还有些走动。三叔公没应她,几步走到镜子前,伸出枯瘦的手指,蘸了点唾沫,
迅速在蒙尘的镜面上画了一个扭曲的符号。那符号一闪而逝,仿佛被镜子吸了进去。
他这才松了口气,但脸色依旧凝重得能滴出水来。“你们两个女娃娃,胆子忒大!
”三叔公转过身,浑浊的眼睛瞪着她们,特别是林晚,“你奶奶临死前千叮万嘱,
叫我把那东西处理掉,没想到……她还是心软,留给了你!更没想到,你真敢把它带回来,
还在这老宅里……胡闹!”他的目光落在林晚掉在一旁的背包上,
那个小木匣子的一角露了出来。“三叔公,那……那到底是什么?
我奶奶她……”林晚声音发颤,劫后余生的恐惧和被指责的委屈交织在一起。
三叔公叹了口气,那口气又长又沉,带着一股浓重的烟味和岁月的腐朽气息。
他拉过一张摇摇晃晃的竹椅坐下,示意她们也坐。“那是‘祀娘’的债。”他点燃一袋旱烟,
辛辣的烟雾在昏暗的房间里弥漫开来,“不是啥庇佑,是祖上造孽,欠下的血债!
”随着三叔公沙哑的叙述,一段被尘封的、血腥而绝望的往事,缓缓揭开。所谓的“祀娘”,
起源于明末清初,南坪镇曾遭遇一场罕见的瘟疫和连年饥荒,死人无数。
当时的族长和几个乡绅,不知从何处请来一个邪师,设下了一个恶毒的祭祀。
他们选中一个八字至阴的少女,将其活活勒死,穿上特制的红嫁衣,放入特制的棺椁,
埋入选定之地,美其名曰“嫁与地府鬼神”,以平息灾厄,换取一方安宁。仪式后,
瘟疫竟真的奇迹般消退。于是,这残忍的习俗便被秘密保留下来,每隔六十年,
在一个特定的癸亥年,就必须从镇中选出符合条件的“阴月阴日”出生的女子,
重复这一仪式,以“延续契约”。“那……那些被选中的女孩……”周婷脸色惨白。
“都死了。”三叔公吐出一口烟圈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,“穿着红嫁衣,
在特定的镜子前……被活活……那邪法,要的就是她们临死前极致的怨气和恐惧,以此为食,
困住她们的魂,让它们成为‘祀娘’的一部分,永世不得超生,以此维系那虚假的安宁。
”林晚浑身冰凉,她想起来笔记本上奶奶写的“阿萍”,还有照片上那个低着头的女子。
“你奶奶那一代,本该轮到林家的一个远房侄女,叫阿萍。”三叔公看向林晚,
“那女娃性子烈,不肯,逃了。结果那一年,镇子里接连出事,死了好几个年轻人……后来,
是你奶奶……她为了保住镇子,或者说,是被宗族逼迫,自愿顶了上去。”林晚呼吸一滞。
“但她没死。”三叔公的眼神变得复杂,“你奶奶,是个厉害角色。
她不知从哪里学来了一些对抗的法子,在仪式最关键的时候,用了某种……替代品,
勉强保住了性命,但也彻底激怒了‘那个东西’。从那以后,她就一直被纠缠,直到死。
”“那东西……到底是什么?”林晚追问。“说不清。”三叔公摇摇头,“不是具体的鬼,
更像是一种……由无数代‘祀娘’的怨念凝聚成的,没有理智,只有吞噬和重复本能的东西。
它依附在那件传承的嫁衣和特定的镜子上,每到轮替之年,就会苏醒,寻找下一个替身。
你奶奶用邪法瞒了它几十年,她死了,压制就弱了。而你,林晚,你的八字,
和你奶奶当年一样,甚至……更‘合适’。”所以,那个包裹,
那些胎毛、指甲、符纸……是奶奶留下的,试图用她血脉相连的气息和某种秘术,
混淆“那个东西”的感知,或者说,为她争取一线生机?
“刚才镜子里……那些影子……”林晚想起那排穿着嫁衣盖着盖头的身影。
“是历代‘祀娘’的残影。”三叔公语气沉重,“它们被困在镜与衣的夹缝里,痛苦,怨恨,
并且本能地想要拉更多同类进去。你差点就被拉进去了!”一阵后怕袭来,
林晚和周婷都打了个寒颤。“那……那现在怎么办?嫁衣扔不掉,烧不坏,它还会来找我的!
”林晚几乎要绝望了。三叔公沉默地抽着烟,烟雾缭绕中,他的脸显得更加晦暗不明。
“你奶奶留下的东西,或许不全是为了保护你。”他忽然说,目光再次投向那个小木匣,